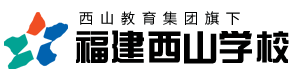有多少教育可以重来

认识浙江温州建设小学校长陈钱林的人,没有不羡慕他的:天赐一对龙凤胎,女儿陈杳16岁即成为南方科技大学首届教改实验班的学生;儿子陈杲未满14岁就被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录取,在读期间,数学成绩全校第一,18岁即到美国读博,师从著名数学家陈秀雄教授和国际数学最高奖“沃尔夫奖”获得者沙利文教授。
令人深思的是,两个孩子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陈校长在家庭教育中所做的自主学习、特别是自主作业实验。
陈杲从小学开始自主学习,两次跳级升入中学后,上午到校上课,下午在家自学,作业自主选择。这样的“另类生长”使他较少受到极端应试的扭曲和污染,更多地呈现出孩子作为“天生的学习者”的一种自然状态。中科大曾因课题之需,邀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陈秀雄教授对少年班的几位学生进行面试,虽然陈杲与其他同学一样没有做出难题,但他却成为唯一被选中的人。陈教授对陈钱林说:“你的孩子了不起!我观察,大部分孩子虽然很聪明,但求同有余,求异不足;做不出题,就感觉很失败,脸红、出汗。而陈杲求异思维很好,且心态平和。做学问就要这样,既有上进心,又有平常心。”中科大少年班学院原院长陈卿老师也坦言:“聪明的孩子多的是,但像陈杲这样‘原生态’的孩子,我们五年才碰到一个!”
某高中进行超常教育实验多年,教师普遍反映,实验班招收的学生虽然智力条件好,但应试痕迹已难以抹去,思维方面的许多“毛病”已经很难“扳”过来。
这让我很感慨。课改推进十年有余,但“应试教育”依然“毁”人不倦。无论是陈杲、陈杳相对“逃离”后的成功,还是实验班孩子深深“陷入”后的无奈,都使我们对教育现状的思考变得更加凝重。也许一切的一切都因为,基础教育于每个人而言只有一次,经历了什么,也就留下了什么,一辈子都难以修复与弥补。想到此,我们便不能不慨叹:有多少教育可以重来?
莫言有言:“文学和科学比确实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它的没有用处正是它伟大的用处”。教育亦然。“急功”,必难获“远利”。也许正是眼前直奔“高分”、“标答”的种种“有用”,才使得教育越来越远离它“伟大的用处”。孩子们习于揣摩权威的意图,而无心谛听真理的声音;他们在求全责备中长大,必然过度关注细枝末节,而疏于探究;那些近乎“条件反射”式的训练,至多只是在对应于感性的“信息”层面徘徊,而与对应于知性的“知识”、对应于理性的“智慧”无涉,在这里,“学习”并没有真正发生;在固有的框架中,一切都是确定的、线性的、封闭的、唯一的,且必须可丁可卯、严丝合缝,十几年下来,孩子们便全然丧失了寻找“有意义的差异”(笔者对“创新”的理解)、寻求对事物做新的解释、寻遍所有可能性的意识与能力,思维钝化了、死寂了、凝固了,“奴性”疯长,“定式”扎根,潜在的思想者变成了机械的匠人?
只有寻求“革命性的突破”,沉疴难愈、广受诟病的基础教育才能摆脱走向绝症的厄运,获得新生。这种突破不是对传统教育的绝对“清空”,也不是方法与技术的单兵冒进,而是通过解放教育生产力而向教育本质的一种回归。
我们看到,所有成功的教育改革无不以行动宣示其坚定的学生立场,这无疑是一种最重要的回归。只有让学生在一种“打开”的状态下成为自觉、自律的学习主体,让他们的思维“欢实”起来,求异、创新、独立思考以及真正的“轻负高质”才可能实现,群体激智、团体体验、不受约束的讨论等等被创造学证明了的有效方法的运用才具备现实的基础。
已故的北京特级教师孙维刚在长达20年的教改实验中创造了诸多奇迹。他带的班,2/ 3的学生入学时成绩低于区重点中学分数线,而毕业时,40名学生中,22人考上北大、清华。他的学生课前不用预习,课上没有笔记,课后没有作业,初三即学完高中三年的数学课程。他的“妙招”就是充分解放学生,造就“强大的大脑”。他创造了解题的“三级跳”:一题多解、多解归一(寻求共性)、多题归一(寻求规律)。几乎所有定理、公式都由学生自己推导,几乎所有大块的时间都用于学生各抒己见、展开论辩??这样带有强烈的探究和发现意味的“高阶学习活动”,是学生形成以“创新能力、问题求解能力、决策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为核心特征的“高阶思维”的重要基础与载体。
近年,类似的改革如星星之火在各地燃起,我们期待,它能早日成为燎原之势。到那时,我们才有可能不再那样沉重地叩问──“有多少教育可以重来?”
(本文选自《中小学管理》2013年第一期卷首语)